从伊斯法罕到美尼蒙当:阿里·埃尔凡的旅程
译自法文
东方,连同它的神秘与苦难,自古以来就滋养着西方的想象力。但我们对当代波斯究竟了解多少?对这片诗歌之地——如今已成为撼动世界秩序的革命舞台——我们又知晓几何?阿里·埃尔凡的作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,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个充满矛盾的伊朗。埃尔凡是一位作家兼电影导演1电影导演:一个事件说明了这位艺术家所面临的直接威胁并加速了他的流亡。当他的第二部电影在伊朗放映时,在场的文化部长在结束时宣布:“唯一还没有洒上不洁者鲜血的白墙就是电影银幕。如果我们处决这个叛徒,让这个银幕变红,所有电影制作人都会明白不能玩弄穆斯林人民的利益”。,1946年生于伊斯法罕,自1981年起被迫流亡法国。他用法语——这门他已熟练掌握的语言——创作的作品,是对一个民族悲剧和流亡者处境的感人见证,其细腻程度实属罕见。
写作即抵抗
在探索那些被暴政和狂热主义的荒谬所折磨的灵魂这一艺术上,许多人将阿里·埃尔凡视为伟大的萨德克·赫达亚特2萨德克·赫达亚特:现代伊朗文学之父,葬于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。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。他的文字冷酷无情,将我们带入一个黑暗压抑、近乎卡夫卡式的世界——一个被“伊玛目们的幻觉哲学”所建立的恐怖统治的社会:无论是《我的妻子是圣女》中受迫害的女性,《世界上最后的诗人》中被压迫的艺术家,还是《天堂的诅咒者》中的受诅咒人物。渗透在这些故事中的死亡不仅仅是暴力本身的死亡,更是产生暴力的极权国家的死亡,这座需要用尸体作水泥才能建立起来的大厦。我们在《无影》中也能找到同样的水泥,这是一部关于两伊战争的有力见证,那场“可怕的屠场”,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壕沟战,吞噬了数十万人的鲜血:
“还有一些志愿者,抱着赴死的念头,挖掘土地造洞,像坟墓一样,他们称之为’上帝恋人的洞房’。
但无论每个人赋予自己临时居所什么意义,他都必须朝着麦加的方向挖洞,而不是面向对面的敌人。”
埃尔凡,阿里。《无影》(Sans ombre),拉图尔代格:黎明出版社,“交叉视角”丛书,2017年。
如果说阿里·埃尔凡没有信仰的喜悦,这是他的缺陷,或者说是他的不幸。但这种不幸源于一个极其严重的原因,我是说他目睹了以宗教名义犯下的罪行,而这些宗教的教义已被扭曲和偏离了其真正的意义,信仰变成了疯狂:
“他不慌不忙地打开一份厚厚的档案,取出一页纸,审视着,突然喊道:
——把这个女人装进麻袋里,向她投石头,直到她像狗一样死去。[…]
他继续着,重复同样的动作,挥舞着那些已经去见上帝的人的文字,抓起另一份[…]。他突然站起来,站在桌子上,像疯子一样喊叫:
——让父亲亲手勒死自己的儿子……”
埃尔凡,阿里。《世界上最后的诗人》(Le Dernier Poète du monde),作者与米歇尔·克里斯托法里合译自波斯语,拉图尔代格:黎明出版社,“黎明口袋书”丛书,1990年。
关于流亡与记忆
流亡是一道永远无法完全愈合的伤口。在《再见美尼蒙当》中,阿里·埃尔凡暂时离开他的故乡波斯,向我们讲述法国——他的避难之地。这部小说是对美尼蒙当街的致敬,这个巴黎的世界性街区,他曾在此生活并从事摄影师工作。这是一部关于“世界迷失者”生活的温柔而时而残酷的编年史,讲述那些像他一样在这个避难所搁浅的社会弃儿。然而,即使在法国,伊朗也从未远离。气味、声音、面孔,一切都让人想起失落的东方。一种为了对抗遗忘而从过去中选择最突出特征的记忆。
每次开始写作时,阿里·埃尔凡都在寻找他早年青春的时光。他品尝着回忆的狂喜,重新找到那些在母语中失落和遗忘的事物的快乐。而且,由于这种重新找回的记忆并不忠实地叙述发生的事情,它才是真正的作家;阿里·埃尔凡是它的第一位读者:
“现在,我懂得它的语言[法语]。但我不想说话。[…]夫人说:’亲爱的,说:茉莉花’。我不想。我想说出我们家里那朵花的名字。它叫什么?为什么我记不起来?那朵长在院子角落的大花。它爬升着,旋转着。它爬过我们家的门,垂落到街上。[…]它叫什么?它很香。夫人又说:’说吧,亲爱的’。我哭了,我哭了……”
埃尔凡,阿里。《世界上最后的诗人》(Le Dernier Poète du monde),作者与米歇尔·克里斯托法里合译自波斯语,拉图尔代格:黎明出版社,“黎明口袋书”丛书,1990年。
阿里·埃尔凡的作品,既独特又普遍,将我们投入一个令人窒息的东方,那里压着触手般神权政治的铅盖。当然,人们可能担心流亡作家尽管违背自己的意愿,却只是在滋养“西方伊斯兰恐惧症”的陈词滥调——这是赫萨姆·诺格雷赫奇《流亡文学是次要文学吗?》的核心论题。但只看到事物这一面的人会错过本质;因为波斯文化一直以来都将分离和流亡作为其最纯净歌声的源泉。这就是鲁米笛子的教训,其崇高的音乐诞生于从故乡芦苇丛中拔出的茎:“聆听芦笛讲述一个故事;它为分离而哀叹:’自从我被从芦苇丛中砍下,我的哀怨让男人和女人呻吟’”。阿里·埃尔凡的声音,就像这支笛子,不是尽管有裂缝而诞生,而是通过裂缝而诞生,将现实的残酷转化为动人的旋律。
延伸阅读
关于《再见美尼蒙当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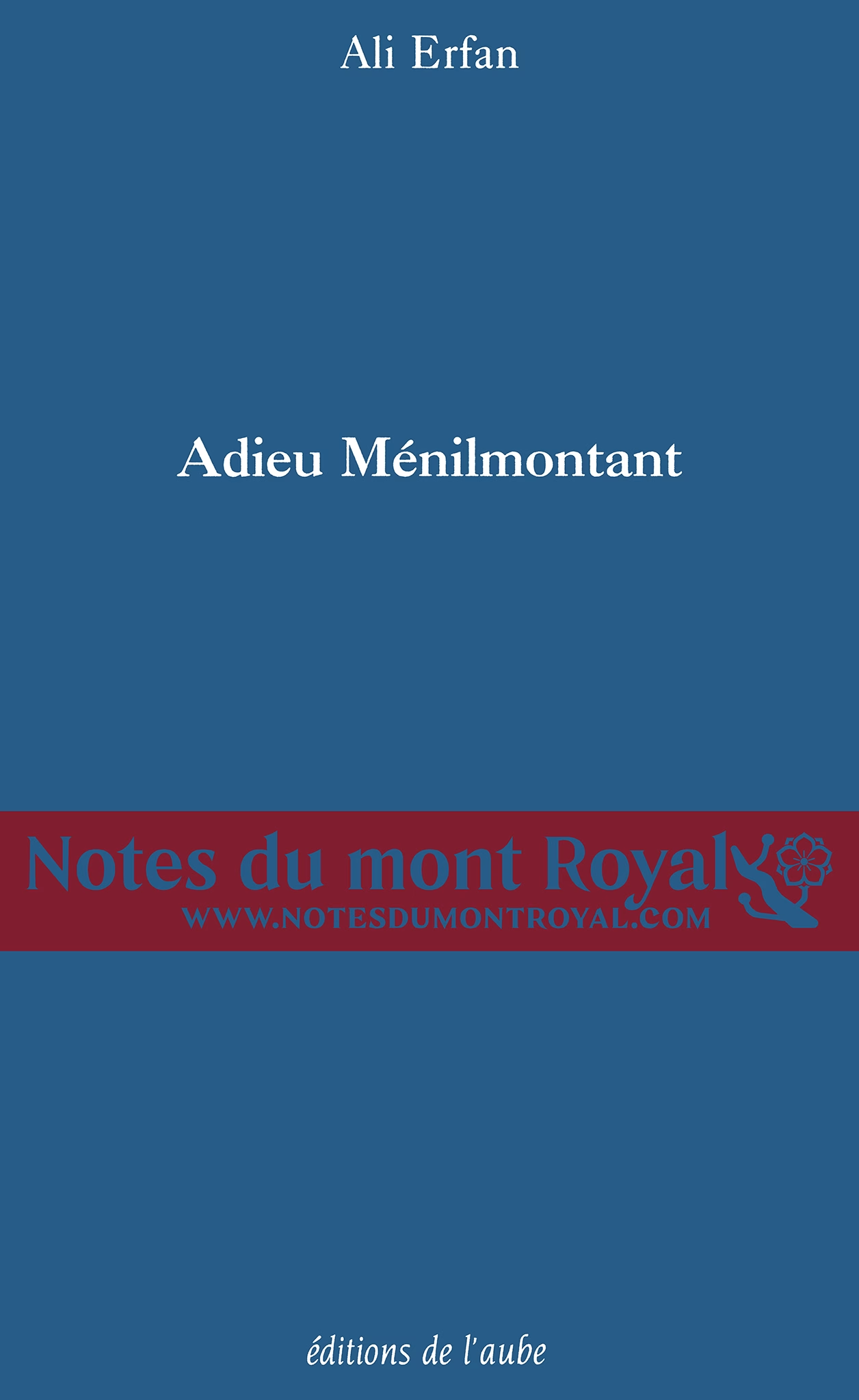
引文
“[…]我爱这条街。它是一个街区的颈静脉,这个街区仍然是世界上所有迷失者的避难所。一代又一代的生活弃儿在这个地方搁浅,就像我一样,熟悉这些地方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陌生。
让我们不要把事情复杂化!渐渐失去了对祖国的所有怀念,同时又不愿属于这座城市,我感觉自己无处可归。我感到自由!”
埃尔凡,阿里。《再见美尼蒙当》(Adieu Ménilmontant),拉图尔代格:黎明出版社,“交叉视角”丛书,2005年。
下载
音频录音
- 阿里·埃尔凡谈《再见美尼蒙当》(法国电视台)。
关于《第602个夜晚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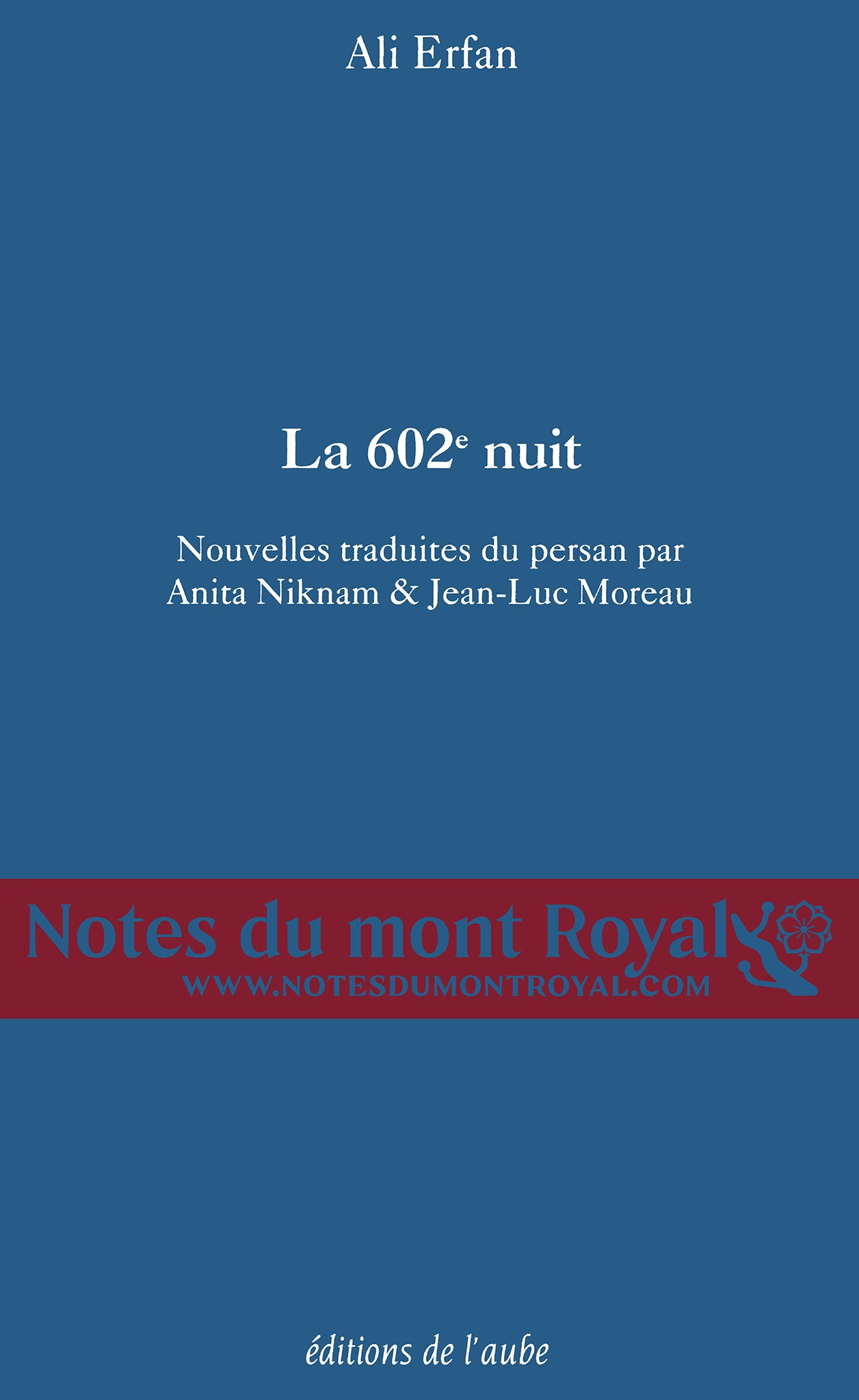
引文
“我直起身子拉开窗帘。一种冷冷的月光和街灯散发的温暖光线的混合物倾泻进房间。她从头到脚都穿着黑色,包括手套。她如此夸张,以至于她的脸在头巾的衬托下显得完全陌生。但当她摘下头巾时,我看到了她的长发,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波浪起伏,一直垂到腰际。我认出了她。她手里还拿着一束花。我微笑着:
——你看我多困惑。
——别开玩笑,这不是给你的。”
埃尔凡,阿里。《第602个夜晚》(La 602e nuit),阿妮塔·尼克南和让-吕克·莫罗译自波斯语,拉图尔代格:黎明出版社,“交叉视角”丛书,2000年。
关于《异教徒之路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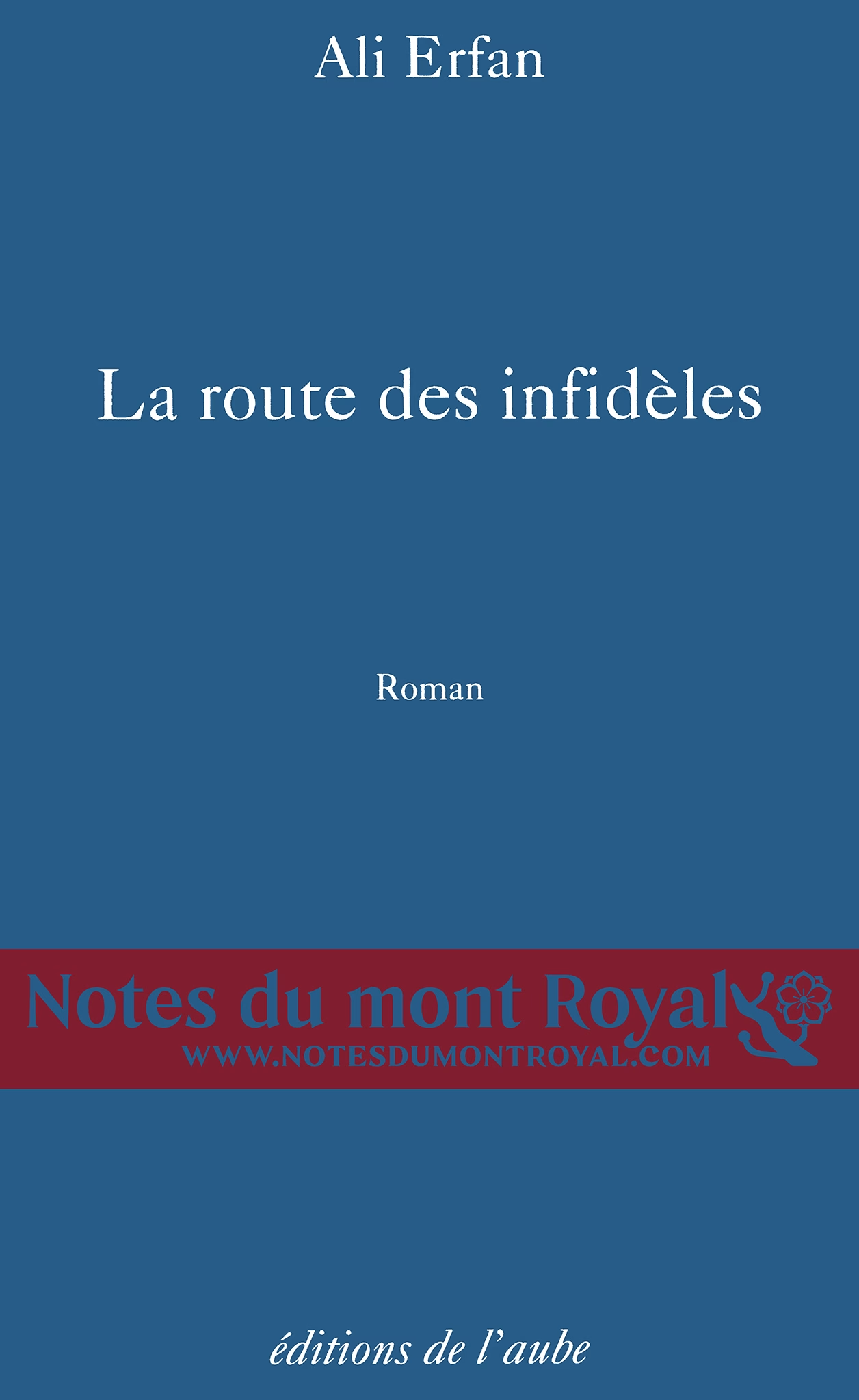
引文
“一个小时以来,我在人群中失去了奥斯塔德。我努力倾听圆顶下朝圣者的谈话。但我只听到模糊和混乱的声音。我越来越迷失。在一个角落里,一位老人正在祈祷。他有着完美的高贵。从远处看,他似乎与世隔绝,面前有着永恒。他吸引着我。当我靠近他,靠在墙边时,我看到他的嘴唇在动。”
埃尔凡,阿里。《异教徒之路》(La Route des infidèles),拉图尔代格:黎明出版社,“交叉视角”丛书,1991年。
关于《世界上最后的诗人》

引文
“我的叙述将像死亡天使一样迅速,当他从窗户或门下的缝隙突然出现,夺走最坏暴君的灵魂,立即从同一条路消失,带走一位诗人的灵魂。”
埃尔凡,阿里。《世界上最后的诗人》(Le Dernier Poète du monde),作者与米歇尔·克里斯托法里合译自波斯语,拉图尔代格:黎明出版社,“黎明口袋书”丛书,1990年。
关于《天堂的诅咒者》

引文
“我没有写这个故事。我是通过邮件收到的。在信封上,有人贴了一个标签,用小字打出了我的名字和巴黎二十区的地址。我打开包裹,发现了一些用潦草的字迹匆忙涂黑的纸页。它们很脏,大小不一。每一页都可能属于不同的世纪。其中一页似乎是从河里撕下来的,因为它完全湿透了。有人把它晾干了,在污渍上重新写了一些被水溶解的词,这些词仍然可以猜到。当然,第一次检查时,我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,就像我没有想到眼泪而不是河水可能使这些线条褪色到看不见。”
埃尔凡,阿里。《天堂的诅咒者》(Les Damnées du paradis),作者与米歇尔·克里斯托法里译自波斯语,拉图尔代格:黎明出版社,1996年(2017年再版)。
关于《我的妻子是圣女》

引文
“我不记得何时何地读过这个故事3这个故事是关于佐贝德城的建立,摘自伊塔洛·卡尔维诺的《看不见的城市》。;但我意识到,我过去的梦想是在读了这篇小说后建立起来的。
故事讲述了生活在彼此遥远地区的人们突然开始做同样的梦:月光在夜晚出现,在一座被遗弃的陌生城市里。一个裸体女人在小巷里奔跑,她有长发,只能看到她的背影。每个做梦的人都在城市里追逐她,但突然间,女人在街角消失了,做梦的人再也无法追上她……”
埃尔凡,阿里。《我的妻子是圣女》(Ma femme est une sainte),拉图尔代格:黎明出版社,“交叉视角”丛书,2002年。
关于《无影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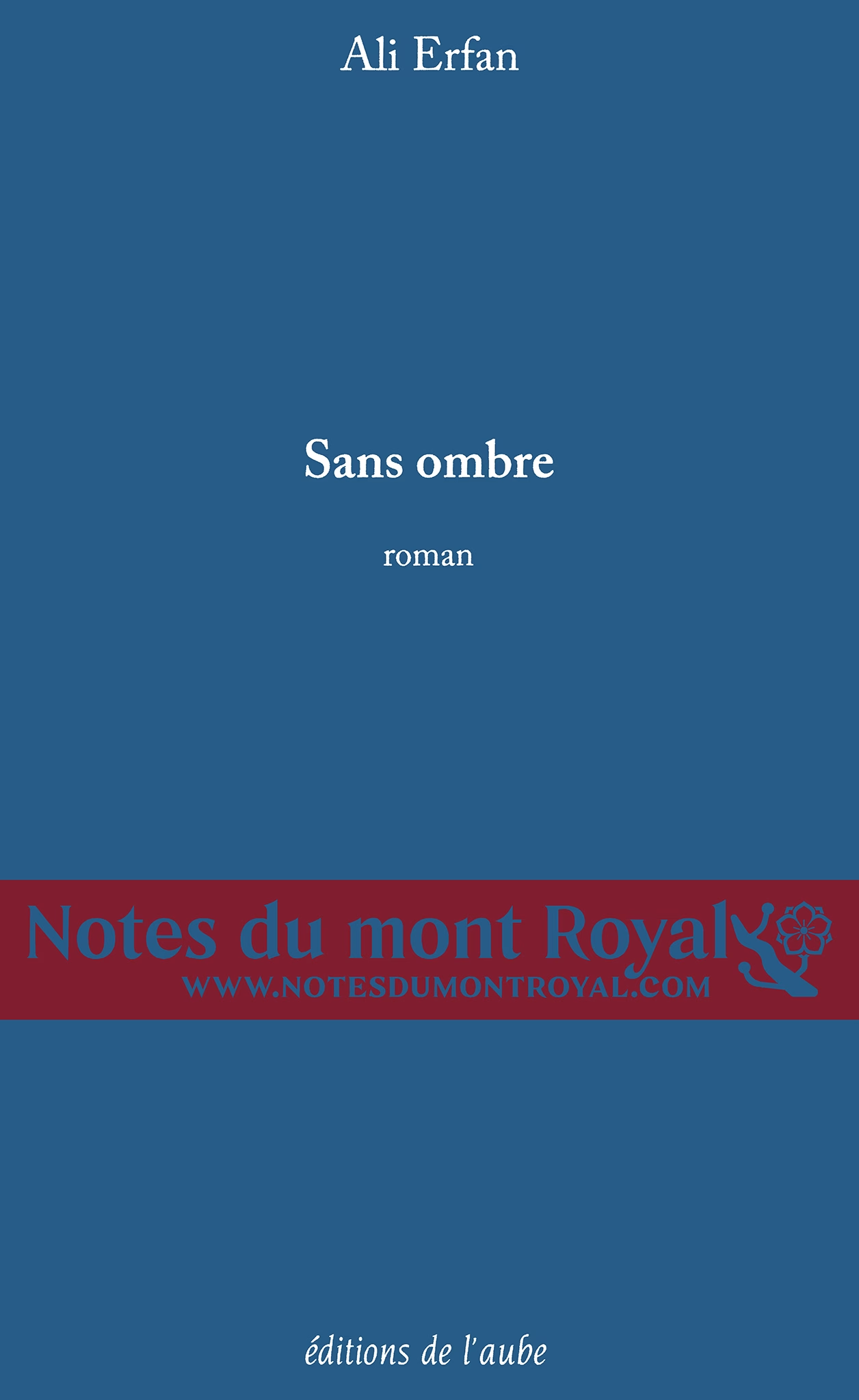
引文
“数百名年轻人在院子里踩踏。越接近招募办公室,骚动就越大。在走廊里,几个小组在激烈争吵。一片混乱:没有人为新志愿者提供信息或指导,甚至连那些戴着臂章的大胡子也在四处奔跑。数百名学生挤在走廊里;他们推搡着[…],开玩笑,鼓掌,但很少有人抗议。人们没有感觉他们要去前线,而是要去里海边野餐。战争很遥远,死亡缺席。”
埃尔凡,阿里。《无影》(Sans ombre),拉图尔代格:黎明出版社,“交叉视角”丛书,2017年。
参考文献
- 达内什瓦尔,埃斯凡迪亚尔。《法波跨文化文学:自80年代以来的文学演变》(La Littérature transculturelle franco-persane : Une évolution littéraire depuis les années 80),莱顿:布里尔出版社,“法语多声部”丛书,2018年。
- 基弗,安妮。“伊斯兰革命的电影”(Le cinéma de la révolution islamique),《青年电影》,第134期,1981年4月,第28-30页。
- 林东,马蒂厄。“阿里·埃尔凡的地狱天堂”(L’Enfer paradisiaque d’Ali Erfan),《解放报》,1996年11月14日。(《解放报》)。
- 林东,马蒂厄。“我们都杀死了赫达亚特”[与阿里·埃尔凡的访谈](Nous avons tous tué Hedayat [Entretien avec Ali Erfan]),《解放报》,1996年10月3日。(《解放报》)。
- 马丁,帕特里斯和德雷韦,克里斯托夫(主编)。《从别处看法语:100次访谈》(La Langue française vue d’ailleurs : 100 entretiens),卡萨布兰卡:塔里克出版社,2001年。
- 诺格雷赫奇,赫萨姆。“流亡文学是次要文学吗?”(La littérature d’exil est-elle une littérature mineure ?),《罗曼语文学论文》,第9期,2014年,第87-95页。(在线超文本文章(HAL))。
- 特拉迪洛斯,让-吕克。“现代人的流亡”[与阿里·埃尔凡的访谈](Exil chez les modernes [Entretien avec Ali Erfan]),《普瓦图-夏朗德时事》,第18期,1992年,第40-41页。(《普瓦图-夏朗德时事》)。
- 特拉迪洛斯,让-吕克。“写作的时间是一种流亡”[与阿里·埃尔凡的访谈](Le temps de l’écriture est un exil [Entretien avec Ali Erfan]),《普瓦图-夏朗德时事》,第53期,2001年,第94-95页。(《普瓦图-夏朗德时事》)。

